一天傍晚,细雨蒙蒙,我隐隐觉得有人在用木杖敲打玻璃。打开窗,并不是奶奶。只是一只水瓢恰在屋檐下,被滴落的雨水击响,哒哒哒,哒哒哒……好像日子悄悄溜走的足音,溜得那么快,一瞬二十年。
二十年前,我还在家乡读书。我的书房也是家里的粮仓,有米、有面,和一方临窗的书桌。傍晚时分,我总伏在书桌前写作业。若天气晴好,我便打开窗户,直面夕阳和暮色中的炊烟;若阴雨连绵,我就把窗户关上,躲避蚊虫和飞溅的雨花。无论晴雨,奶奶总会在晚饭后悄悄拐过屋角,敲响我的窗户,递给我一包吃食。
有时雨大,奶奶仍来。她不打伞,头顶一件外套,拄一根柴堆里抽出的木杖,蹒跚而来。雨大如豆,打透薄衣裳,她把身形蜷得更小一些,把怀里的吃食护好,任水珠顺着灰黑的头发浸入皱纹,顺势流下、滴落,又落地成雨。雨幕中,奶奶的脚步是无声的。我总在心中惦记着她要来,又总在她敲响玻璃后才意识到她当真来了。
我劝她以后别再冒雨过来,“淋感冒,当心又犯气管炎”,奶奶摆摆手,不让我把这些挂在心上。放下吃的后,她也不在窗前停留,或去里屋找我妈说说话,或转身就回自己屋子。她离开时,任她推搡、拒绝,我也定要打上伞,搀着她走过砖砌的院子、高高低低的台阶和一条无灯的、湿滑的窄路,送她回去。
这条窄路,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而过。小时候,奶奶拉着我的手,常走这条小路,送我回来;长大后,我搀着奶奶的手,常走这条小路,送她过去。下雨天,路滑,两侧的屋檐又往下泄水,很难走,但我和奶奶走得多了,便知道走到哪里该躲,走到哪里该跳,自有一番冒险的乐趣。
后来,我去外地上学,每次假日结束离家时,奶奶总泪眼婆娑地送我,给我带上一堆好吃的。看到她抹泪,我就想到她淋雨,想到她在雨中蹒跚着走来。我心里不忍,便骗她过几天周末了就回,她数着日子盼,一盼就是半年。那时,我是多么的无知又残忍呀,竟没有意识到,对于一个老人来说,是没有几个半年可盼的。
奶奶去世的时候,也是一个雨季,但那几天没有下雨。我想象着,她是在一片雨过天晴的晚霞下,与我告别的。一道冲破云层的、金灿灿的霞光照着她,她回头看看我,然后拄着木杖走了。我总觉得,她还会拄着木杖来。
窗外,天空下起思念的雨,我看到远处的河边,有人在烧纸钱。中元节已经过去很久了,或许是因为家乡路远,思念的故人要跋涉几日才能到来,所以纪念才晚来吧。我默默地想,奶奶走得那么慢,又下着雨,她何时才能到呀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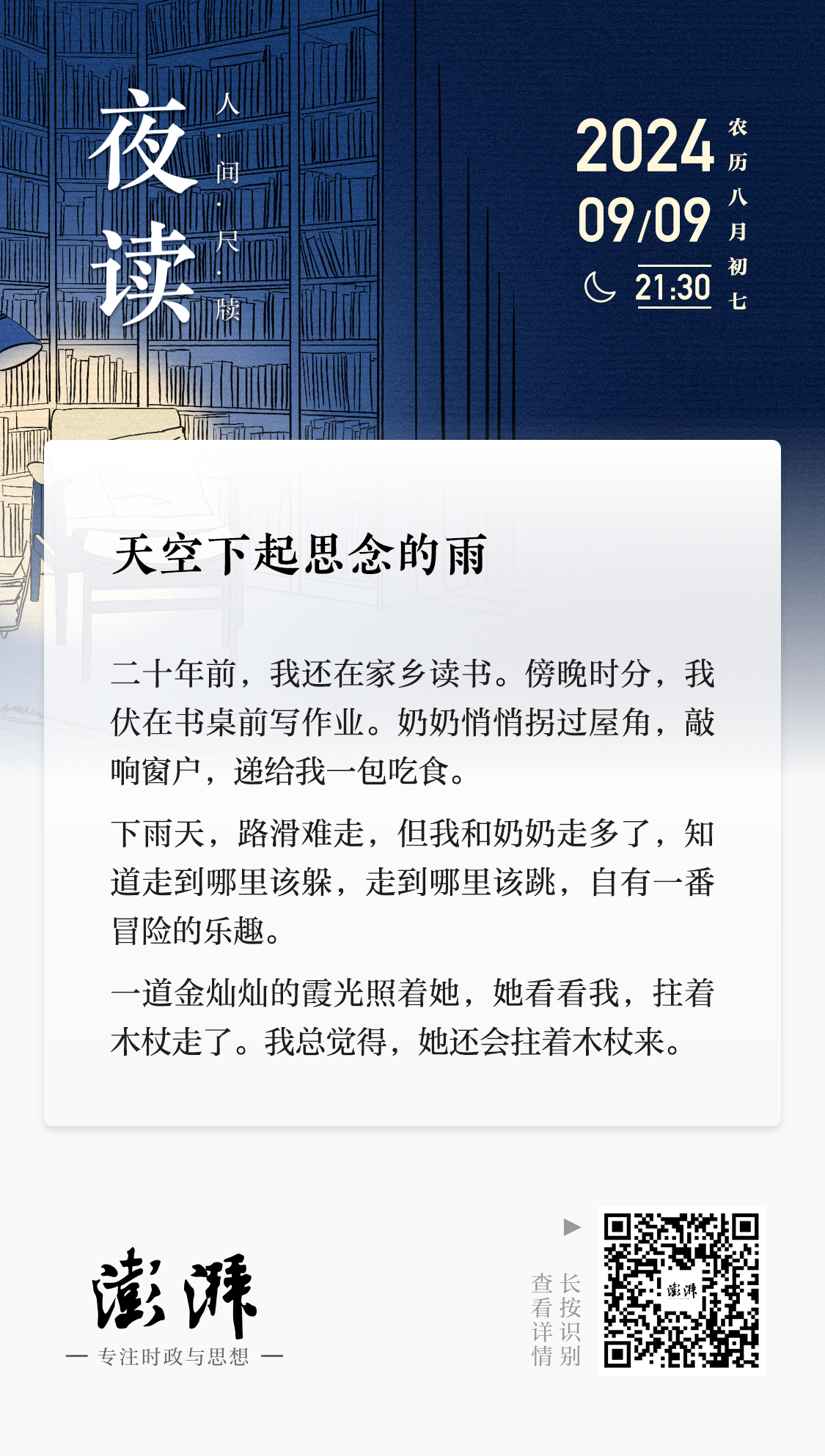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